内容提要 在查韦斯执政的14年间,石油繁荣和积极的再分配政策大大降低了贫困率,减少了贫富差距,由此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但高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模式和过度亲穷人的公共政策导致委内瑞拉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这给其继任者马杜罗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加之缺乏国家共识,马杜罗政府正遭遇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面围困,国家治理能力愈加脆弱。委内瑞拉的未来因此充满相当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 委内瑞拉 社会结构变迁 国家治理能力 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委内瑞拉都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由此带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新的社会阶层——新兴中产阶级[1]的崛起。这意味着社会总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由此要求政府与时俱进,调整过分倾斜的亲贫政策,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新分配模式。但在查韦斯执政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其后期及其继任者马杜罗时期,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重要的调整,以致经济和社会政策高度政治化,社会两极分裂日趋严重,国家治理能力趋弱。
一 社会结构变迁和国家治理能力
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它反映两个层面的变化[2]: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看,社会结构变迁意味着社会失范和失序的风险增加,因为阶层结构尚未定型,仍处于变动之中。如果不能对这种结构变动作出有效的回应和控制,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斯梅尔塞(Neil Joseph Smelser)认为,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的六大因素都是次第形成的,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力下降是触动集体行动的最后一根稻草。[3]
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但总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主要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手段的多样性,认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也包括公民社会,特别是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4]从狭义上讲,主要是将“国家治理能力”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即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大众需要,平衡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潜在及现有力量和能量的总和。[5]本文主要指其狭义概念,即政府治理能力。
二 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
过去20年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基尼系数稳定下降,职业分布更加向上集中,受教育年限渐次上升,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石油繁荣和再分配政策,二者提供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基础。
(一) 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
委内瑞拉的社会结构变迁源于两大动力:相对稳定的石油繁荣和长期亲穷人的再分配政策。
首先,石油繁荣是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委内瑞拉是一个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石油探明储量高达2970万桶,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6]石油是委内瑞拉国民经济的支柱,出口收入的95%以上、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石油行业[7]。过去10多年间,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升,从2000年每桶37美元暴涨至2011年每桶107美元[8]。在过去15年间,委内瑞拉经济除偶有衰退外,大部分时期保持稳定和高增长,创造了盛极一时的石油繁荣。
其次,积极的再分配政策助推社会结构的优化。进入20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有意识地在经济政策中嵌入社会政策目标,以实现“增长中再分配”,主要手段是通过公共支出对财政资源进行再分配。查韦斯时期,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被用于社会支出。从1999~2000年度到2007~2008年度,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攀升,从13.9%上升到20.6%,均超过同期拉美平均水平。其中,教育支出的增长趋势显著。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连续两个年度(1999~2000年度和2000~2001年度)比拉美平均数高出1倍,分别达到8.9%和11.1%,2007~2008年度更是高达14.8%。[9]
(二)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
1. 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首先,贫困人口显著下降。1999年委内瑞拉有近一半(49.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在随后10多年间,总体上呈稳定下降态势,到2012年贫困人口的比重已降至25.4%。[10]其次,收入分配明显改善。1997~2012年,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其间虽偶有反弹,但持续并不太久。这一时期,基尼系数从0.507降至0.405,降幅超过25%,远超地区平均水平(不足7%)。最后,不同收入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变化反映出明显的政策亲贫性。收入最低的社会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增幅最大,而收入最高的两个十分位数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占比降幅最大,从1997年的32.8%降至2012年的23.7%,降幅超过38%。[11]
2. 职业结构
经济繁荣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推动着委内瑞拉职业结构的变化。“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间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12]。1998~2010年,委内瑞拉的职业结构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13],即传统中产阶级的上层(职业和专业人士)和中层(行政和管理人员)的比重保持稳定上升,而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办事员)明显萎缩,其中很大一部分向下流动进入了中产阶级的下层——商业服务业人员。因此,中产阶级下层比重增加明显主要源于两个方向的作用:来自上一职业阶层的向下流动和更低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由此形成了一个脆弱的、不稳定的新兴中产阶层。该阶层在社会中的位置尚未结构化,潜藏着不稳定的风险。
3. 教育结构
委内瑞拉教育领域的进步非常明显,特别是高等教育。根据拉美经委会的数据,1999~2012年间,中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47.8%增加到74.3%。高等教育发展更快,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28.3%提高到2009年的78.1%。[14]教育的稳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改善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据显示,1997~2011年,15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最显著的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增幅,其中受过13年及以上教育的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增加最快,从1997年的16.7%飙升至2011年的28.6%,增幅达到71.2%。[15]
三 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治理挑战
过去10多年间,委内瑞拉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结构紧张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同时又是‘冲突与混乱’的根源”[16]。从委内瑞拉的具体现实来看,“结构紧张”越来越表现为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内生矛盾,二是政府设计的两极分化战略所致。
(一) 中产阶级的崛起
在委内瑞拉,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是新的社会阶层新兴中产阶级的扩大。2012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发现[17],过去10年间,拉美的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54%,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新兴中产阶级。该报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但遗憾的是缺乏委内瑞拉的国别数据。科拉莱斯和弗兰德沿用该报告的界定标准和研究思路,同时结合拉美经委会收入分配十分位数的数据,计算得出委内瑞拉收入十分位数中每个收入群体的人均日收入水平。为便于分析,科拉莱斯又对人均日收入在10~50美元之间界定为中产阶级的标准进行了细分类,人均日收入在10~15美元之间为下中产阶级;人均日收入在15~30美元之间为中中产阶级;而人均日收入在30~50美元之间则为上中产阶级。
结果发现了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20多年间,委内瑞拉的社会阶层分布实现了从以中下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向以新兴中产阶级(下中产和中中产)占主体的结构性转变。第二,新兴中产阶级的扩张主要发生在2004~2006年间。2006年以前仍有大约40%的委内瑞拉人属于比较脆弱的社会阶层(多数是穷人),但2007~2012年间最脆弱阶层的比重大大下降了,只有一个十分位数。收入较低的两个群体(第2和第3个收入十分位数)向上流动进入了下中产阶级。[18]第三,尽管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新主体,但其收入在2007~2012年期间几乎没有增加,甚至在一定年份还有些下降。考虑到这一时期委内瑞拉平均27%的年通货膨胀率,其压力可想而知。中产阶级的相当部分,特别是其下层和中下层因此变得比较脆弱,格雷厄姆将该群体称之为“失望的成就者”。[19]这个群体的通常特征是:收入中等、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居平均水平之上;他们既不再像穷人那样继续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等社会计划,也无法像富人那样有能力放弃低质量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尽管实现了一定的社会流动,但仍心存不满,对继续向上流动的前景感到悲观。
(二) 无序政治参与的扩大
经济增长推动了中间阶层的扩大,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活力,但拥有一些独特的价值诉求。彭福尔德等发现,与中东和东欧相比,拉美的中产阶级虽然没有特殊的价值观和偏好,但有两个与其他发展中地区截然不同的特征。第一,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倾向。这意味着该地区的中间阶层不仅仅关注经济和安全需求,更关注社会化需求,比如自由、生活质量和决策话语权等。第二,拉美的中间阶层更具理想主义情怀,渴望成功的期望值较高。与中间阶层的扩大及其不断上升的期望值相匹配的应当是社会制度及其结构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和空间。[20]
这两大特性意味着,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的中产阶级具有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只不过,在政党和公共机构日益不被信任的情况下,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充满着无序。委内瑞拉的情况更加极端,其经济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此背景下,政治生活的日益对立导致政府限制过度参与,但这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权利意识觉醒的新兴中产阶级更容易选择抵抗,造成社会不稳定。这种局面之形成,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于疾速的社会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制度的发展却又过于缓慢造成的”[21]。就整个拉美而言,当前社会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根源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及其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委内瑞拉除了具有这种共性之外,还有其独特性,即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被压制以及对政策倾向性、政策不透明和政治生活无序的不满。
(三) 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
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是查韦斯及其继任者马杜罗时期的典型特征。但这种分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经济和社会领域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造成的,而被视为是查韦斯的一种策略设计和安排[22],目的是获得穷人占多数的选民。查韦斯正是通过其倡导的“参与式民众主义”和“使命”等社会计划,实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动员。
查韦斯的两极分化策略在2001~2004年间获得选举收益,穷人可以保证执政联盟获得足够多的基础选票,但中产阶级群体因为利益受损或者没有获得切实的利益,对此表示抗拒。到2007~2009年,分化策略却已经无法为执政联盟提供较高的选举回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布和收入分布发生了深刻变化,回归到一种更加相称、均衡的状态。这种新状态背后的动因是意识形态上持中间立场的中产阶级的群体性兴起,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中层和下层成为委内瑞拉社会的主体。
到查韦斯执政后期,两极分化策略不仅进一步失灵,而且已经从主观意志使然固化为一种客观存在,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结构化的阶级分野。马杜罗时期,委内瑞拉社会分裂更加明显,但其间隐现一个新的动向,即不仅中产阶级反对政府,甚至之前的政府支持者也开始逐渐不再支持。2000~2013年的4次大选中,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得票差距都在逐步缩小,到2013年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2个百分点。[23]对执政党来说,这种趋势值得警惕,预示着执政党在未来一个时期甚至会更加艰难。这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 执政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穷人追随政府的意愿下降。调查表明,2013年学生和反对派掀起抗议活动时,问及是否会响应马杜罗的呼吁上街捍卫政府时,只有21.3%受访者表示肯定,而高达76.4%人则表示不会响应号召。而认为马杜罗呼吁上街反游行以保卫政府的举动是正确的比例还不足30%,更有67.3%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号召本身就是错误的。[24]但在更早的2002年和2007年抗议期间,当政府需要政治帮助时,就成功地动员了中下群体组织反示威活动。
第二, 政治宽容度明显提高。“美洲晴雨表”的最新调查发现,委内瑞拉的政治宽容指数[25]高达61.8,是拉美所有国家中得分最高的。这说明当前委内瑞拉社会各阶层对包括批评政府在内的诸项政治权利支持力度最高,也最具政治包容精神,同时也从反面说明公众越来越不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做法。2012年以来,委内瑞拉的政治宽容度稳定提高,反映该指数的各项指标得分均接近或超过60。这意味着委内瑞拉政府压制反对声音的举动将会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这无疑会限制和削弱政府治理能力及手段。
四 国家治理的失灵
在查韦斯执政的14年间,统治合法性几乎完全系于其个人魅力和石油美元。凭借这两大支撑,查韦斯获得了中下阶层选民的支持。然而,个人魅力和石油繁荣是最靠不住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也因其缺乏相对稳定的制度支撑而不可持续。
(一) 经济不安全及其风险
虽然历史上委内瑞拉的经济体系并不健全,但到查韦斯时期经济的单一性更加明显,即过于依赖石油。到2012年,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96%和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依靠石油;而在查韦斯上台的前一年(1998年),石油出口还只占委内瑞拉出口额的77%[26]。石油业的大发展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1998年委内瑞拉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7.4%,到2012年上半年已降至14.2%,这一数字是委内瑞拉1965年的水平。[27]客观而言,委内瑞拉的“去工业化”并非始于查韦斯,但从1999年以来,这种趋势却始终是非常明显的。工业能力退化导致委内瑞拉只能依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这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链条。结果,到2014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量价齐跌后,众症并发的局面初露端倪。
首先,短缺现象日趋严重。2007年短缺指数高达24.7%,2014年2月更是达到创历史纪录的28%[28],以致政府最后停止更新物价短缺数据。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加剧。查韦斯执政的第一年曾成功地将年通胀率从1998年的35.8%降至1999年的23.5%,之后数年均保持相对稳定的下降(除了2003年升至31.1%),但之后通胀率一路攀升,从2007年的18.7%骤增至2014年的55.5%,7年间增幅高达19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http://www.imf.org外汇市场也剧烈变动。2003年,为阻止资本抽逃,维持玻利瓦尔的稳定性,查韦斯实施了严格的货币管制,结果导致货币黑市。2013年,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63个强势玻利瓦尔,而黑市价格则高出10倍以上。
(二) 公共安全风险急剧增加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是暴力犯罪较少的国家,但到2010年已沦为全球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委内瑞拉的暴力犯罪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1993年,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的“加拉加斯大骚乱”和1992年军事政变。这个时期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8到10万分之20。第二个阶段是1994~1998年,凶杀率仍然维持在10万分之20左右。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今,凶杀率增至10万分之57(2010年)和10万分之82(2014年)。[29]
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使社会各阶层都难以免遭不法侵害,但显然有一定经济地位又缺乏足够自我保护能力的中间层是公共安全恶化最主要的牺牲品。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INE)的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20%(Estrato I)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20%(Estrato V)的人口遭受各种类型犯罪侵害的比重最低,而犯罪侵害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间层,特别是中下层(见图1)。比如,抢劫案的受害者50.3%是第4社会阶层(Estrato IV),22.8%是第3社会阶层(Estrato III);绑架案的受害者97.87%是中间阶层,其中第2和第4社会阶层受侵害比重最高,分别是27.9%和50.1%。这主要是由于富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强,而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下层成为最主要的侵害对象。
图1 委内瑞拉各类犯罪的侵害对象(按社会阶层)

资料来源:“Encuesta Nacional de Victimización y Percepción de Seguridad Ciudadana 2009 (ENVPSC-2009)”,INE, Caracas, Mayo de 2010,p.70. http://www.dere.chos.org.ve
普遍蔓延的犯罪活动严重冲击了委内瑞拉的社会秩序,导致公众安全感普遍降低。2013年的调查表明,拉美是盖洛普法律和秩序指数得分最低的地区,而委内瑞拉的表现不仅是拉美地区最低的,也是全世界最低的。“拉美晴雨表”的调查也表明,2013年有47%的委内瑞拉人将公共安全列为本国最严重的问题,这一数字比拉美平均数高出24个百分点。[30]
(三) 社会冲突烈度显著增加
社会结构变迁意味着利益的分化,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都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冲突观察”报告显示[31],从2011年开始,尤其是查韦斯逝世以来,委内瑞拉的社会冲突愈演愈烈。
第一,社会冲突爆发的次数,除2013年略有下降外,总体上呈持续增加态势,2014年和2015年年初的增幅尤其显著(见图2)。2011年委内瑞拉共爆发示威抗议事件5388起,2013年降至4410起,但到2014年,社会冲突事件急剧攀升至9286起。最新数据显示,未来一个时期委内瑞拉社会抗议和冲突有持续扩大的可能性。2015年1月,委内瑞拉全国至少爆发了518起抗议活动,平均每天17起,比2014年同期(445起)高出16%。从历史规律来看,新年第一个月爆发社会冲突的次数较低,但2015年则打破了这个规律,抗议频度高于前4年同期水平。
图2 2011~2014年委内瑞拉的社会抗议次数

资料来源:“El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Conflictividad Social (OVCS)”. http://www.observatoriodeconflictos.org.ve
第二,抗议诉求多元化,但大多数诉求与社会权利相关而非政治性的。总体而言,委内瑞拉社会冲突的主要动因有六个,即抗议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短缺,捍卫劳工权利,要求有尊严的住房和基本服务,主张公民安全和言论自由等权利,提供教育服务,以及抗议政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2~2014年期间,有两种抗议诉求突然爆发,即物质短缺和抗议政府。总体上看,除2014年外,其他时段包括2015年1月份,社会冲突的诉求70%甚至80%以上同社会权利相关,即要求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2014年可谓政治抗议年,全年共发生抗议活动9286起,平均每天25起,是过去10年的最高纪录,其中52%是反对政府和捍卫政治权利。到2015年年初,政治性抗议减少,80%的诉求都围绕社会和民生权利展开。但近期第008610号法令将抗议入罪化无疑将加剧这种社会冲突。
(四) 腐败日趋严重,公共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腐败在委内瑞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但在查韦斯时期,腐败问题日趋严重。查韦斯执政初期,委内瑞拉的腐败问题略有缓解,反映腐败严重程度的清廉指数从1995年的2.66上升到2001年的2.80,略好于查韦斯执政前的表现,但好景不长。之后腐败问题日益恶化,清廉指数持续下降,从2001年的2.80降至2014年的1.9。委内瑞拉的清廉度排名不仅落后于全球,甚至在拉美地区也仅好于海地,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32]
腐败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从2007年开始,委内瑞拉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滑,从当年的63%降至2013年的39%,创造了历史新低。司法系统在委内瑞拉人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糟糕。2006~2013年间,委内瑞拉人对法院和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度,除2009年低于50%以外,其他时期均保持在50%以上,2013年更是达到这个时期的最高纪录61%。[33]最新发布的2014年世界法治指数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在99个国家和地区中综合排名倒数第一。在限制政府权力、监管执法、刑事司法等指标上,不仅在拉美地区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中,乃至全球均名列倒数第一。[34]
(五) 人力资本外流
委内瑞拉历史上曾是世界移民的理想港湾[35],但过去20年间,委内瑞拉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反向流动[36]。1998~2013年,超过150万委内瑞拉人(约占其总人口的4%~6%)移民海外。[37]这些海外移民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职业阶层[38],90%拥有学士以上学位,其中40%拥有硕士学位,12%拥有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经历。从其职业构成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政治流亡者,目前在美国约有9000人,向欧盟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数量也在上升;(2)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技术人员和管理阶层,约有2万人,其中多数是因为2002~2003年参加反对查韦斯的游行活动而被驱逐或被迫离开;(3)企业家;(4)会计师和管理阶层;(5)医生和护士阶层;(6)知识界,特别是教育和科技人才。[39]过去5年间,西蒙·玻利瓦尔大学(USB)有240名教授放弃教职出国;大约700名教职员工在2011~2012年离开委内瑞拉中央大学(UCV);到2013年年底苏利亚大学(LUZ)有1577个教师岗位空岗。[40]
目前这种人才外流的悲剧还在继续。2014年民调机构“数据分析”的调查显示,有10%的委内瑞拉人计划在不远的将来离开委内瑞拉。这一数字比两年前增加了1倍,也超过了过去10年间委内瑞拉向外移民的两个高峰时期,即2002年政变后和2004年公投后。[41]
委内瑞拉大量向外移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在拉美地区,传统上向外移民的主力是社会下层,目的主要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在委内瑞拉,已经移民或者计划向外移民的人群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42],他们选择“用脚投票”的主要原因[43]包括国家缺乏中长期的连贯政策、公民安全无法保障(诸多研究表明这是移民的首要原因)、就业质量不高、通货膨胀严重、汇率管制和货币持续贬值、公共服务质量日趋低下、腐败以及国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六) 国家治理能力日趋弱化
在查韦斯执政的中后期,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日渐不稳,政府各方面的管控能力日趋弱化,而到2013年已面临严峻形势。这一点从世界治理指数的纵横比较中可见一斑。
纵向来看,委内瑞拉的国家治理能力日渐趋弱。世界治理指数的变动趋势显示(见图3),从查韦斯执政前一年,即1998年以来到2013年,世界治理指数的各项指标[44]基本上呈持续下降态势。其中,下降速度最快、恶化最严重的领域依次是法治指数(从23分降至不足1分)、监管质量指数(从40分降至3分)、腐败控制指数(从2000年的峰值35分降至2013年的7分)。但这个时期,拉美地区的世界治理指数均稳定地保持在中间偏上水平或有所提高,与委内瑞拉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3 1998~2013年委内瑞拉世界治理指数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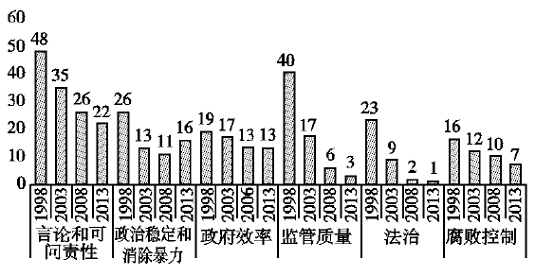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治理指数数据库。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reports
横向来看,委内瑞拉的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远远落后于拉美地区,而且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相距甚远[45]。以最新的2013年数据分析来看,委内瑞拉世界治理指数的各项指标都远低于拉美平均数,也远远落后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委内瑞拉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世界治理指数平均水平相比,委内瑞拉相差甚远。比如法治指数只有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1/49,监管质量只有其1/16强,腐败控制只有其1/7强,政府效能只有其1/4强。最后,委内瑞拉世界治理指数的各项指标在拉美国家中均处于最低或接近最低水平。
五 结论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委内瑞拉经济增长带动了社会结构变迁,创造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需求。这意味着执政者需要革新思维,适时地将政策从传统的亲贫增长模式转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增长[46]。但查韦斯及马杜罗政府显然都没有或不愿意正视这一点,而不断地依靠权力意志强化治理的权力建设而非能力建设,以致国家濒于不可治理。当前,外部环境恶化导致的新风险可能给马杜罗的统治能力带来致命一击。
首先,国民认同急剧下降。最新调查表明,总统马杜罗在2014年拉美总统支持率排名中倒数第一,只得34. 3分,比拉美平均水平低近20分。[47]马杜罗支持率的下降与委内瑞拉政治宽容度的大幅提升有密切关系,因为委内瑞拉人更加包容,也更加认同“反对的权利”。
其次,政治支持基础或将发生重大变动。独立机构的调查发现,最近两年的经济衰退导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回升到接近1998年的水平(45%),2014年,委内瑞拉共有48. 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下。[48]拉美经委会新近发布的报告也侧证了这种变化:2013年拉美地区只有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和赤贫率均出现大幅上升,其中,贫困率从2012年的25. 4%升至32. 1 % 。[49]可以预测,2015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将再创新高,因为近两年来推动贫困上升的因素,比如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恶性膨胀、实际工资购买力剧烈下降等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
最后,中间阶层和社会下层的抗议有相互交织甚至合流的可能性。未来两到三年,委内瑞拉经济不太可能出现明显好转,反而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经济衰退最容易给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构成威胁,因其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限。穷人是政府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财政收入萎缩首先冲击的是社会下层。这可能会激发下层群体的不满,但也会减少对政府的经济依附。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同时满足中间阶层和最脆弱群体的需要,就可能爆发社会抗议,且有相互交织,甚至出现合流的可能性。这对马杜罗政府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就目前而言,委内瑞拉能否避免陷入不可治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放弃门户之见和意识形态对立,通过对话凝聚共识,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发出声音、分享权力,以缔造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共治局面,从而逐渐走出当前的危机。
(责任编辑 高涵)
收稿日期:2015-02-28
作者简介:郭存海,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
[1] 本文使用了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层的概念,其含义均为middle class,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新兴中产阶级在文中主要指中产阶级的中下层。
[2] 侯佩旭、范士陈:《海南岛社会变迁扫描——以新中国成立为研究起点》,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7期,第144页。
[3] 六大因素是: 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动员、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参见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第64页。
[4] 姚亮:《国家治理能力研究新动向》,载《党政干部参考》,2014年第16期,第15页。
[5] 施雪华:《政府综合治理能力论》,载《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8页。
[6]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4.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7]Matt Ferchen, “Opportunity for Beijing and Washington in Venezuela’s Oil Crisis”, in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12
[8]EIA,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Real Prices Viewer”. http://www.eia.gov/forecasts/steo/realprices/
[9]CEPAL,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de Chile, 2014, Cuadro 32, Cuadro 33, Cuadro 35,and Cuadro 39 http://interwp.cepal.org/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14/es/index.asp. 部分数据是作者基于原数据计算得出。
[10]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数据库。 http://estadisticas.cepal.org/cepalstat/WEB_CEPALSTAT/Portada.asp?idioma=i
[11]CEPAL,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Santiago de Chile, 2014, Cuadro 14. http://interwp.cepal.org/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14/es/index.asp.部分数据是作者基于原数据计算得出。
[12]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71页。
[13]郭存海:《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4]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数据库。http://interwp.cepal.org/cepalstat/WEB_cepalstat/estadisticasIndicadores.asp
[15]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数据库。http://interwp.cepal.org/cepalstat/WEB_cepalstat/estadisticasIndicadores.asp
[16]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21页。
[17] Francisco H. G. Ferreira et al., 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November 2012.
[18] Javier Corrales, “Venezuela’s Middle Ground”, in Foreign Policy, April 22, 2014.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4/22
[19] Carol Graham and Len Goff,“Frustrated Achievers, Protests, and Unhappiness in 3 Charts”, June 17,2014.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4/06
[20] Michael Penfold y Guillermo Rodríguez Guzmán, “La Creciente pero Vulnerable Clase Media de América Latina: Patrones de Expansión”, Valores y Preferencias, Serie Políticas Públicas y 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CAF, No.17,2014
[21]郭存海:《巴西中产阶级“革命”的逻辑》,载《东方早报》,2013年7月23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7/23/1038560.shtml
[22] Javier Corrales, “Why Polariz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 RationalChoice Analysis of GovernmentOpposition Relations under Hugo Chávez”, in Jonathan Eastwood and Thomas Ponniah(eds.), Revolution in Venezuel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11.
[23] “Consejo Nacional Electoral de Venezuela”. http://www. Cne.gob.ve
[24] Venebarometro, Estudio especial de marzo, 2014
[25]政治宽容指数(Political Tolerance Index)反映的是对批评体制、抗议、投票、言论自由和竞选公职的支持度和容忍度。政治宽容指数介于0(最不宽容)和100(最宽容)之间。参见:Mariana Rodríguez and Elizabeth J. Zechmeister, “Amid Low Evaluations of Maduro’s Performance, Tolerance of Regime Critics Grows in Venezuela”, in AmericasBarometer:Topical Brief, March 2, 2015.
[26] World Bank,“Venezuela Overview”.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venezuela/overview
[27] “Venezuela’s Industry Slumps to Levels Recorded Fifty Years Ago”,in El Universal. http://m.eluniversal.com/economia/121119
[28] Sendai Zea,“Venezuelan Central Bank Admits Sky.High Inflation”, in PanAm Post.http://panampost.com/sendai-zea/2014/09/15
[29] Roberto Brice.o-León, “Tres Fases de la Violencia Homicida en Venezuela”, en Ciência & Saúde Coletiva, Vol.17, No.12, diciembre 2012,pp.3233-3242. http://www.redalyc.org/pdf/630/63024 424008.pdf
[30] Latinobarómetro, 2013, p.63. http://www.latinobarometro.org
[31] Informe Conflictividad Social en Venezuela en 2011,2012,2013,2014 y enero de 2015, El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Conflictividad Social (OVCS). http://www.observatoriodeconflictos.org.ve。本节数据均取自该组织报告。
[32] 33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http://www.transparency.org
[34] WJP Rule of Law Index 2014 http://data. Worldjusticeproject.org/#/index/VEN
[35]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来自欧洲的移民和80年代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移民。
[36]委内瑞拉移民的反向流动经历了3个关键的节点:1983年、1992年和2002年。
[37] Antonio Maria Delgado, “Venezuela Agobiada por la Fuga Masiva de Cerebros”. http://www.elnuevoherald.com/noticias/mundo/america-latina/venezuela-es/article2039010.html
[38] Peralta Arias y Rubén Dario, Diáspora del Talento. Migración y Educación en Venezuela: Análisis y Propuestas, Editoriales Varias, Caracas, 2014,转引自Tomas Paez, “El Talento se Fuga de Venezuela”. http://www.tomaspaez.com/pagwp/?p=411.
[39] Iván De la Vega y Claudia Vargas, “Emigración Intelectual y General en Venezuela: Un Mirada Desde dos Fuentes de Información”, en Bitácora-e, Revista Electrónica Latinoamericana de Estudios Sociales, Históricos y Culturales de la Ciencia y la Tecnología,No.1,2014.
[40] 41“Venezuela: Pobres Condiciones trasxodo de Científicos”. http://www.scidev.net/america-latina/educacion/noticias
[42] “Ten Percent of Venezuelans Are Taking Steps for Emigrating”,in El Universal,August 16, 2014http://www.eluniversal. com/nacional-y-politica/140816,
[43] Arminda Hanoi Reyes Reyes, El Caso Venezuela: Como un País Receptor de Inmigrantes Se Convierte en un Pueblo de Emigrantes, Tesis de Maestría, 2014, Universidad de Nebraska
[44] 世界治理指数是世界银行基于十几家来源综合计算得出言论与可问责性、政治稳定与消除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等六项指标的得分,实行百分制,是目前世界上评估国家治理能力最权威的指标。本节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治理指数数据库。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
[45] World Governance Index (WGI). http://info.worldbank. org/governance/wgi/index.aspx#reports
[46] Nancy Birdsall, “The Ma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clusive MiddleClass Growth”, IFPRI, January 14, 2008. http://www.ifpri.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oc63essay01.pdf
[47] Mariana Rodrfguez and Eli zabeth J. Zechmeister, "Amid Low Evaluations of Madum's Perfor mance, Tolerance of Regime Critics Grows in Venezuela",Figure 1,in AmericasBarometer; Topical Brief, March 2,2015.
[48]Luis Pedro Espana N.,Pobreza y Programas Sociales , Encuesta.snbre C,nn4irinnP.s rlr Virla Venvnwla 2074. U(:AB&UCV&USB
[49]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krica latina 2014 , Santiago de Chile, p.66.